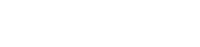翌日。
雪宝贪睡赖床不愿起身,柳寂也不叫她,任由宝贝往足了睡。
她巳正二刻才睡醒,一醒马上跳下床,穿好衣服就想找爹爹。
雨早就停了,庭院里的地砖半湿不湿,瞅着有些潮意,不大干燥。
怕爹爹看到会说她,雪宝不敢赤脚踩到院里,于是扒在绣房门沿向外张望。
透过竹帘隐约窥到书房的一角雾蓝衣袂,才安下心,折返回屋穿鞋袜。
洗漱梳妆过后,喝了小半碗酒酿圆子,吃了一个爹爹早上才做的牡丹饼。
还想吃山药糕,柳寂却不允许她再吃了,撤走碗碟,端上药碗,“马上午时,这会儿吃多了,午饭该欠着了。”
“哦。”
雪宝犹豫许久,才皱着眉毛捧起药碗,打算一饮而尽。
药汁入口却不像昨天那般苦涩,反而甜丝丝的。
诶?
柳寂轻刮一下挺翘秀气的小琼鼻,笑道:“爹爹煮药的时候加了红枣和蜂蜜。”
甚至担心红枣蜂蜜与药性相冲,不敢私自乱加,清晨专到胡大夫那里请教过了,才敢加一点进去与药同煮。
雪宝心里也甜丝丝的,漱了口很乖巧地帮爹爹洗干净碗筷,然后一起到书房饮茶,跟爹爹学念诗。
一首《剑器行》,父女两个读来两种心境。
雪宝好奇什么样的剑舞能“动四方”,又能令“观者如山色沮丧,天地为之久低昂”。
又好奇“来如雷霆收震怒,罢如江海凝清光”的舞姿究竟是怎样的。
爹爹剑术超绝,不知道爹爹会不会这种剑舞,可这公孙大娘好像是名女子?
女子舞得动人好看,男子舞来却未必了吧?
柳寂带雪宝一起重读这几行幼年时便深爱不已的诗文,落点却在“感时抚事增惋伤”和“五十年间似反掌”上面。
那几句提醒他半生已过,而这半生恰又潦草难以落笔。
纵然早已抛弃道德礼法,欲要无耻霸占这娇憨可爱的小人儿。
可年岁无情,柳寂此刻忍不住暗想:他真能爱她一生、护她一生么?若他几年、十几年后便死去,留她孤苦无依呢?又该如何?
毕竟他们中间隔了近二十载的岁月,难以跨越,如何跨越?
想着便心烦意乱起来,难不成要将好不容易才得到的心肝宝贝拱手于人?
眼睁睁看她嫁给和她年龄相当的什么青年才俊,在别人怀里度过一生?
不可能!
天下岂可有如此放屁之事!!
他柳孤言岂会行如此放屁之事!!!
要放弃宝贝,除非他死了!
现在就死了!
尸骨被道旁野狗叼了去,啃了吃了,肉化泥,骨化灰。
神魂泯灭,无法再想着她、念着她的时候,才有那么一天。
狗男人自己跟自己生气,神色阴晴不定,含着明显的暴戾之气。
雪宝手轻轻盖住他的,小声问道:“剑器是什么样的舞?爹爹会不会呀?我想看。”
被温软小手牵住,柳寂才回神。
呵,庸人自扰。
想那些有的没的作甚?他年长宝贝二十岁,便努力比她多活二十年。
总要一生一世守着她,护着她,疼她爱她。
他捉起羊脂玉润的手放到唇边细细亲吻,柔声回答:“爹爹不会。”
“剑器非剑舞,近来一些不学无术之辈总以为剑器便是舞剑,所造图册、所编舞蹈皆是一人或多人执剑而舞,孰不知剑器只是名中带剑,实则乃赤手空拳而舞。”
“哦。”雪宝认真点头,原来是这样,接着又有些遗憾地说:“爹爹,那现在是不是已经看不到剑器是怎样舞的了?”
柳寂摸摸她的脑袋,笑,“长安还有人会舞,以后带宝儿去拜访。”
“长安?我也可以去吗?”雪宝连平山县都没出过。
“当然。”
长安,故事里的长安,遥远的长安,雪宝开始憧憬起来。
此时有人敲门来访,头发缺了一小块的秃头小雪宝急忙避到屏风后面。
摆明了既不想见客人,又想听人家和爹爹聊什么。
来者叫陈宾,字山客,年近叁旬,是隔壁景州的一名书商。
大门开启之后,陈宾先朝柳寂拱手见礼,然后从随从肩上接过一只布包褡裢,挥手命其退下,自己随柳寂到书房坐定。
“陈兄此番前来是为书的事?”柳寂奉上盏茶,问道。
“是。”陈宾扶了扶茶盏,道过一声谢后,方从褡裢里取出一部书,道:“晚辈来和先生商量诗文集刊印的事,前日已勘校完毕,这是样书,请先生过目。若是无误,晚辈即刻安排雕版刻印。”
柳寂接过样书,从头翻看。
前半部是诗集,后半部文集,统共六百七十八篇。
刻板样式则是每页二十八行,每行二十四字,版心双鱼尾,版框四周双边,以缝缋法装订。
陈宾道:“编订时按年份排的顺序,日后收录先生的其他文章,要增订也容易。”
柳寂大致翻过一遍,合上书,指着书封,臭着脸道:“《南北集》?”
看那神情架势,就差指着人家的鼻子骂:这是什么不读书的人取的狗屁不通的名字。
“正是。”陈宾冒着冷汗客气回答:“晚辈几人思量再叁,想着先生行迹广阔,走南游北,非其他词汇所能概括,才定下此名。”
柳寂略思索一番,“就叫《濯雪堂集》,作者署名的话,濯雪堂主人亦或濯雪堂居士都可。”
他还当上居士了,还有脸自称居士。
整天色欲熏心,心心念念记挂的都是女儿的小嫩屄,不是想看就是想亲亲摸摸,更想早日提屌干进去。
谁家善男信女这般恬不知耻、这般贪欢好色?还居士。
陈宾面带疑惑,“这‘濯雪堂’,不知有何典故?”
“我这书房就叫濯雪堂。”
陈宾望向帘外,进来的时候也没见门口挂什么匾额,也从未听说,于是道:“门上好似未挂匾额?”
接着歉意道:“哦!也可能是晚辈进来得匆忙,未及细看。”
“匾额前几日才写好,送去裱刻,还没好。”老男人张嘴就来,信口胡诌。
雪宝也是头一回听说家里的书房还有名字,还叫濯雪堂,想是爹爹现取的,小丫头躲在屏风后面偷笑。
濯、雪、堂,雪,雪,是她!
好看的梨涡浮在脸颊,越来越深,越来越深,甚至忍不住“咯咯”笑出声来。
听到笑声陈宾才知屏风后面有人,柳寂淡淡道:“小女在后面小憩。”
“哦,哦,那晚辈先告辞,回去就安排改名的事,后面再来叨扰。”
“先不忙,我稍后写一篇《濯雪堂记》让人送过去,可将其置于首篇。”
这......编年法编订的集子,突来一篇放在开头,有些乱了章法。
陈宾为难,却也不好说什么,想来也能算是个序吧?
只得答应下来,“好,静候先生佳作。”说罢便起身拱手离去了。
雪宝一下从屏风后跳出来,拿起桌上的样书欣喜翻看,“爹爹的诗文要刊印了?那岂不是可以有机会文章与天地同老,随滚滚江河万古奔流啦。”
小雪宝也开始学着说文绉绉的话,开心至极。
“文章自然是千古事。”
“那爹爹的姓名呢?是不是也会千秋万代流传?像故事里的那些人一样。”
“千秋万岁名要来何用?”柳寂在宝贝头上轻拍一记,温柔笑道:“爹爹只想要宝儿。”
随即提笔,龙飞凤舞写下一联:
濯足濯缨功名无用堪笑人间沧浪尽
雪暗雪明明德有成始知世上是非轻
他还明德有成了,要不说文人的笔墨最会粉饰,无非是和女儿的感情终于开花结果了,到他笔下就成了“明德有成”。
无德背德之人也敢标榜自己明德有成,也是多亏了脸皮比别人厚。
柳寂使唤雪宝:“宝宝过来将此联抄录一遍,明日爹爹找人裱刻,好挂在书房门口。”
“啊?我吗爹爹?”雪宝有些不敢置信。
爹爹的书法那样好,却要挂她的字,羞赧低下头,“我写字不好看,丑丑的,爹爹知道的。”
“宝儿的字稚拙天然,才得真趣,挂在上面正合适,听话。”
雪宝这才到书案边上,询问爹爹该写成多大,蘸墨将那对联认真抄写一遍。
最后又在坏爹爹的哄唆之下题了匾额,正是“濯雪堂”叁字。
ps:对联是我自己瞎写的,出了格律或者写得不好只代表我菜,不代表老柳真实水平,他大文豪,他牛逼,是柠某耽误了他,他搞黄和牛逼着就行,菜和锅都是我的hhhhhh
雪宝贪睡赖床不愿起身,柳寂也不叫她,任由宝贝往足了睡。
她巳正二刻才睡醒,一醒马上跳下床,穿好衣服就想找爹爹。
雨早就停了,庭院里的地砖半湿不湿,瞅着有些潮意,不大干燥。
怕爹爹看到会说她,雪宝不敢赤脚踩到院里,于是扒在绣房门沿向外张望。
透过竹帘隐约窥到书房的一角雾蓝衣袂,才安下心,折返回屋穿鞋袜。
洗漱梳妆过后,喝了小半碗酒酿圆子,吃了一个爹爹早上才做的牡丹饼。
还想吃山药糕,柳寂却不允许她再吃了,撤走碗碟,端上药碗,“马上午时,这会儿吃多了,午饭该欠着了。”
“哦。”
雪宝犹豫许久,才皱着眉毛捧起药碗,打算一饮而尽。
药汁入口却不像昨天那般苦涩,反而甜丝丝的。
诶?
柳寂轻刮一下挺翘秀气的小琼鼻,笑道:“爹爹煮药的时候加了红枣和蜂蜜。”
甚至担心红枣蜂蜜与药性相冲,不敢私自乱加,清晨专到胡大夫那里请教过了,才敢加一点进去与药同煮。
雪宝心里也甜丝丝的,漱了口很乖巧地帮爹爹洗干净碗筷,然后一起到书房饮茶,跟爹爹学念诗。
一首《剑器行》,父女两个读来两种心境。
雪宝好奇什么样的剑舞能“动四方”,又能令“观者如山色沮丧,天地为之久低昂”。
又好奇“来如雷霆收震怒,罢如江海凝清光”的舞姿究竟是怎样的。
爹爹剑术超绝,不知道爹爹会不会这种剑舞,可这公孙大娘好像是名女子?
女子舞得动人好看,男子舞来却未必了吧?
柳寂带雪宝一起重读这几行幼年时便深爱不已的诗文,落点却在“感时抚事增惋伤”和“五十年间似反掌”上面。
那几句提醒他半生已过,而这半生恰又潦草难以落笔。
纵然早已抛弃道德礼法,欲要无耻霸占这娇憨可爱的小人儿。
可年岁无情,柳寂此刻忍不住暗想:他真能爱她一生、护她一生么?若他几年、十几年后便死去,留她孤苦无依呢?又该如何?
毕竟他们中间隔了近二十载的岁月,难以跨越,如何跨越?
想着便心烦意乱起来,难不成要将好不容易才得到的心肝宝贝拱手于人?
眼睁睁看她嫁给和她年龄相当的什么青年才俊,在别人怀里度过一生?
不可能!
天下岂可有如此放屁之事!!
他柳孤言岂会行如此放屁之事!!!
要放弃宝贝,除非他死了!
现在就死了!
尸骨被道旁野狗叼了去,啃了吃了,肉化泥,骨化灰。
神魂泯灭,无法再想着她、念着她的时候,才有那么一天。
狗男人自己跟自己生气,神色阴晴不定,含着明显的暴戾之气。
雪宝手轻轻盖住他的,小声问道:“剑器是什么样的舞?爹爹会不会呀?我想看。”
被温软小手牵住,柳寂才回神。
呵,庸人自扰。
想那些有的没的作甚?他年长宝贝二十岁,便努力比她多活二十年。
总要一生一世守着她,护着她,疼她爱她。
他捉起羊脂玉润的手放到唇边细细亲吻,柔声回答:“爹爹不会。”
“剑器非剑舞,近来一些不学无术之辈总以为剑器便是舞剑,所造图册、所编舞蹈皆是一人或多人执剑而舞,孰不知剑器只是名中带剑,实则乃赤手空拳而舞。”
“哦。”雪宝认真点头,原来是这样,接着又有些遗憾地说:“爹爹,那现在是不是已经看不到剑器是怎样舞的了?”
柳寂摸摸她的脑袋,笑,“长安还有人会舞,以后带宝儿去拜访。”
“长安?我也可以去吗?”雪宝连平山县都没出过。
“当然。”
长安,故事里的长安,遥远的长安,雪宝开始憧憬起来。
此时有人敲门来访,头发缺了一小块的秃头小雪宝急忙避到屏风后面。
摆明了既不想见客人,又想听人家和爹爹聊什么。
来者叫陈宾,字山客,年近叁旬,是隔壁景州的一名书商。
大门开启之后,陈宾先朝柳寂拱手见礼,然后从随从肩上接过一只布包褡裢,挥手命其退下,自己随柳寂到书房坐定。
“陈兄此番前来是为书的事?”柳寂奉上盏茶,问道。
“是。”陈宾扶了扶茶盏,道过一声谢后,方从褡裢里取出一部书,道:“晚辈来和先生商量诗文集刊印的事,前日已勘校完毕,这是样书,请先生过目。若是无误,晚辈即刻安排雕版刻印。”
柳寂接过样书,从头翻看。
前半部是诗集,后半部文集,统共六百七十八篇。
刻板样式则是每页二十八行,每行二十四字,版心双鱼尾,版框四周双边,以缝缋法装订。
陈宾道:“编订时按年份排的顺序,日后收录先生的其他文章,要增订也容易。”
柳寂大致翻过一遍,合上书,指着书封,臭着脸道:“《南北集》?”
看那神情架势,就差指着人家的鼻子骂:这是什么不读书的人取的狗屁不通的名字。
“正是。”陈宾冒着冷汗客气回答:“晚辈几人思量再叁,想着先生行迹广阔,走南游北,非其他词汇所能概括,才定下此名。”
柳寂略思索一番,“就叫《濯雪堂集》,作者署名的话,濯雪堂主人亦或濯雪堂居士都可。”
他还当上居士了,还有脸自称居士。
整天色欲熏心,心心念念记挂的都是女儿的小嫩屄,不是想看就是想亲亲摸摸,更想早日提屌干进去。
谁家善男信女这般恬不知耻、这般贪欢好色?还居士。
陈宾面带疑惑,“这‘濯雪堂’,不知有何典故?”
“我这书房就叫濯雪堂。”
陈宾望向帘外,进来的时候也没见门口挂什么匾额,也从未听说,于是道:“门上好似未挂匾额?”
接着歉意道:“哦!也可能是晚辈进来得匆忙,未及细看。”
“匾额前几日才写好,送去裱刻,还没好。”老男人张嘴就来,信口胡诌。
雪宝也是头一回听说家里的书房还有名字,还叫濯雪堂,想是爹爹现取的,小丫头躲在屏风后面偷笑。
濯、雪、堂,雪,雪,是她!
好看的梨涡浮在脸颊,越来越深,越来越深,甚至忍不住“咯咯”笑出声来。
听到笑声陈宾才知屏风后面有人,柳寂淡淡道:“小女在后面小憩。”
“哦,哦,那晚辈先告辞,回去就安排改名的事,后面再来叨扰。”
“先不忙,我稍后写一篇《濯雪堂记》让人送过去,可将其置于首篇。”
这......编年法编订的集子,突来一篇放在开头,有些乱了章法。
陈宾为难,却也不好说什么,想来也能算是个序吧?
只得答应下来,“好,静候先生佳作。”说罢便起身拱手离去了。
雪宝一下从屏风后跳出来,拿起桌上的样书欣喜翻看,“爹爹的诗文要刊印了?那岂不是可以有机会文章与天地同老,随滚滚江河万古奔流啦。”
小雪宝也开始学着说文绉绉的话,开心至极。
“文章自然是千古事。”
“那爹爹的姓名呢?是不是也会千秋万代流传?像故事里的那些人一样。”
“千秋万岁名要来何用?”柳寂在宝贝头上轻拍一记,温柔笑道:“爹爹只想要宝儿。”
随即提笔,龙飞凤舞写下一联:
濯足濯缨功名无用堪笑人间沧浪尽
雪暗雪明明德有成始知世上是非轻
他还明德有成了,要不说文人的笔墨最会粉饰,无非是和女儿的感情终于开花结果了,到他笔下就成了“明德有成”。
无德背德之人也敢标榜自己明德有成,也是多亏了脸皮比别人厚。
柳寂使唤雪宝:“宝宝过来将此联抄录一遍,明日爹爹找人裱刻,好挂在书房门口。”
“啊?我吗爹爹?”雪宝有些不敢置信。
爹爹的书法那样好,却要挂她的字,羞赧低下头,“我写字不好看,丑丑的,爹爹知道的。”
“宝儿的字稚拙天然,才得真趣,挂在上面正合适,听话。”
雪宝这才到书案边上,询问爹爹该写成多大,蘸墨将那对联认真抄写一遍。
最后又在坏爹爹的哄唆之下题了匾额,正是“濯雪堂”叁字。
ps:对联是我自己瞎写的,出了格律或者写得不好只代表我菜,不代表老柳真实水平,他大文豪,他牛逼,是柠某耽误了他,他搞黄和牛逼着就行,菜和锅都是我的hhhhhh